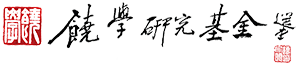前頁
前頁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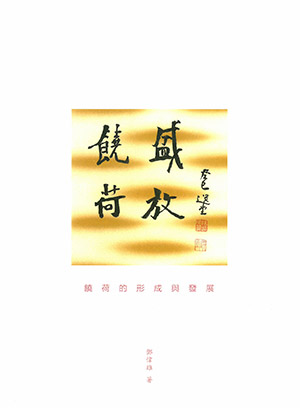
出版:2014
編著:鄧偉雄
出版社: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;香港
本書為研究「饒荷」的專著,講述了饒宗頤教授繪寫荷花的起因及發展,以及他寫荷花的種種形式。荷花是饒教授八十以後繪畫創作的主要題材之一,此書亦收集了他所開創荷花繪畫的新體制。
「饒荷」的形成 — 代序
在中國的花卉之中,荷花有一個很特別的地位,尤其是自東漢白馬馱經、佛教西來中土以後,荷花更是有一種宗教意義。因為在釋教經典之中,荷花有神聖的象徵。阿彌陀經中,西方淨土的池塘中就種著各種金荷銀荷;釋迦佛祖也坐在九品蓮臺之上;觀世音菩薩的蓮座,更有著慈悲的意思。
敦煌壁畫大部分都與佛教有關,故荷花也是在壁畫上出現最多的花卉。從最早的北魏洞窟之中,不論是藻井,或是佛像,都有荷花圖案或荷花的形象;隋、唐兩代的菩薩畫像、或飛天之中,大多數都是手持荷花,或站立,或安坐於蓮臺之上。
除了敦煌出土的絹畫之外,最早見於紙絹上的荷花,應該是宋代畫院紈扇上的工筆紅荷。自此以後,花卉畫家無不寫荷花;元代的趙孟頫(1254-1322),明代文衡山(1470-1559)、唐六如(1470-1523)、陳老蓮(1598-1652)、明末四僧中的石濤(1642-1707或1718)及八大(約1626-約1705),都是寫荷花的高手。到了清初惲南田(1633-1690)以沒骨法寫荷,更是出色當行。近代吳昌碩(1844-1927)的金石荷花、于非闇(1889-1959)的雙勾重設荷花,亦各有特色。張大千(1899-1983)把荷花寫出了如山水畫一般的雄渾氣勢,更開前人未有的格局。凡此種種,主要是因為周敦頤(1017-1073)寫了〈愛蓮說〉:「蓮,花之君子者也。」賦予荷花一種「出淤泥而不染」的清高品格。
饒宗頤教授自七十年代較多繪寫花卉,以荷花為主。早年的荷花,筆法近於四僧中之石濤。在八十年代初,饒教授在天津博物館得見八大山人的荷花巨構〈河上花卷〉,他說,「看見這一卷畫,有一種驚心動魄的感覺。」因為這一卷荷花的雄壯氣勢,是古來寫荷花者所未見。自此,他就開始在荷花的氣勢上著力,這一點可說是與張大千的創作趨向不謀而合。筆者認為,可能是因為這個緣故,從九十年代開始,饒教授自然而然地就追求荷花的新表現方式。
筆者見過饒教授以梁楷(生卒年不詳)潑墨潑色的方法寫荷葉,並配以雙勾荷花;也見過饒教授把惲南田的沒骨法加入釋法常(生卒年不詳)的減筆法來寫荷花;亦見過他寫敦煌各個時期的荷花形象;他也嘗試用敦煌白畫的方式來描繪荷花。在經過了各種的嘗試,並加上他一直認為藝術與學術必須互益互補的想法後,終於點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,就是他所寫的荷花,是「他心中的荷花形象」。這一個觀念,就是「饒荷」形成的重要標誌。
從新世紀開始,饒教授的荷花可謂踏進了「無入而不自得」的地步,他所用的筆法、色彩、甚至構圖,很多都是古人所未有涉筆者。他有一些作品以金或銀墨來勾寫,然後填以紅色;他亦用其他方法勾寫,包括一些以敦煌白畫筆法所勾勒敦煌各朝代的荷花造型;有些是先以潑墨潑色的形式,粗略地寫出荷花及荷葉的形象,然後用金或墨來勾外型;亦有完全用潑色、減筆的筆法來作大寫意荷花,有些則在大片潑墨的荷葉上,以金書寫題記,形成很獨特的構圖。故此,他這十多年來的荷花,可說是千變萬化,成為他獨有的「饒荷」。
「饒荷」在他近年的繪畫中,可謂開前人所未有之境界,也是現代鑑藏家最為注目的一種畫風。